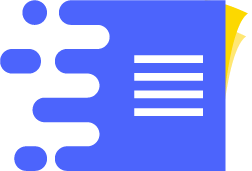红学的困境:学术研究和大众之间差100个娱乐头条
2010-07-26 │
东方早报
[摘要]这个世纪,红学开始红得尴尬。红学家突然发现,很多普通读者、观众已不站在自己这边,学界与大众之间的文化联系及信任似乎不再。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产品之间,恐怕差了100个娱乐头条。
红楼梦研究一度被推广为一项“全民运动”,而本世纪以来,热闹的红学似乎红得有些尴尬。1987年版的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受到了红学会的大力支持,3个编剧都是红学会推荐的。
虽然位列20世纪中国的三大显学,20世纪上半叶,《红楼梦》研究尚不脱知识阶层的逸趣雅好或智力游戏,却因其中一位爱好者毛泽东,在中国大陆被推广普及为全民运动。此后很长时间里,中国红学研究的学术交锋里,或显或隐流露着政治较量的兵刃气。
“文革”之后,红学在索隐、考据、阶级论的道路外,重新回归小说本身。在知识仍带有光环的时代里,红学是专家的,也是普罗大众的,《红楼梦学刊》作为一本学术刊物,第一辑发行达8.5万册。同时,学界亦积极向大众提供文化产品,1987年的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受当时红学潮流影响,结局设置以探佚结果取代了流传更广的后四十回,虽然对此改编红学家内部犹有争议,老百姓却只管对着电视机唏嘘垂泪。
但这个世纪,红学开始红得尴尬。索隐派借助强势媒体“卷土重来”,民间研究者、爱好者借网络展开言说空间,红学界作为共同的对立面,在双方的相互印证中,被树为一个压制异见的强势组织。同时,在学术生产后劲不足、缺乏有效诉诸大众的文化产品、应对时代转型的反应迟钝,以及一个学术团体面对权力资本的微妙处境的共同作用下,以中国红楼梦学会为代表的红学研究界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。
这种遭遇可能只是当下学术界困境的一个投影,但红学因其红极一时,成为最容易被捕捉的案例。起朱楼的盛况依稀,宴宾客的场面犹在,下一步哪怕楼塌了,也不失为传统悲剧收梢;但在这个时代,还可能出现更残忍的结局:或漠不关心,或当个笑话。
89岁的冯其庸坐在主席台上,身边是86岁的李希凡,以及被李希凡称作“小胡”的71岁的胡德平。这是11月23日“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大会暨学术讨论会”的开幕式,这位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声音洪亮思路清晰地作了10分钟的发言,在回顾了20世纪红学发展,表达了新世纪的新期待后,他略作停顿,全场掌声适时响起,然而冯其庸接着说:“但扩展思路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不是让大家去想入非非,学术研究要认真踏实、实事求是。”
1954年向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发难而受到毛泽东肯定的李希凡,批评了目前存在的“秦学”(刘心武对《红楼梦》的猜谜式研究)、否认曹雪芹著书以及彻底否定程高本的观点:“学术需要百家争鸣,以便让我们更好地接受《红楼梦》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,但争鸣不是奇谈怪论,是要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。”
用自己的话说,冯其庸已经“看不清,对着耳朵说才能听到;李希凡同志比我好一些,他的听力还行”,但这些年的红学聚讼,他们看来还是了然于心,并有所回应。然而这一场景,印证的更像是红学研究在当下的传播困境:在场的都是“自己人”,与批驳对象没有直接对话机会,意见往往只能由媒体一鳞半爪地转达。最残忍的是,连刘心武都见好就收地不提红学会很多年,红学界的老先生们却还是习惯性地摆出了对阵的架势。对他们来说,这也许是对待学术论争的应有态度,但在习惯了一切都以信息乃至以景观观之的当代观众,看上去也许更像一群白头老者在“闲坐说玄宗”。
学术争端或危机公关
“2005年开始,红学出现了乱象。”原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胡文彬说。
与其说是乱象,不如说是暴露了红学家们捉襟见肘的危机公关能力,虽然原本在他们的学术训练中,从来不需要这一项。这一年的4月,刘心武登上央视《百家讲坛》“揭秘《红楼梦》”。这不是这个2001年创办的科教节目第一次普及《红楼梦》,也不是这位知名小说家首次发表红学观点,但当刘心武通过央视成竹在胸地把一部名著当套娃拆解,还真的取出了一组更神秘的“秦学”,全国人民都看呆了。
红学界的应对仍按照惯有逻辑运行:2006年第1期的《红楼梦学刊》为驳斥“刘心武揭秘《红楼梦》”的观点与方法,刊发了一组文章。学者们或以为用9篇文章从论据论证到思想源流各个角度能对刘的学说逐一攻破,匡扶正统。但意外的是,此举一出,加上之前各人零零散散的媒体表态,反而使“主流红学界”仗势欺人的学阀形象深入人心。
这或许是这个时代学术争鸣的代价。1992年刘心武的《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》在《红楼梦学刊》发表,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固是大为激赏,也有人展开争鸣,对于驳诘观点,刘心武在《“秦学”探佚的四个层次》自道:“我确实非常珍惜陈诏、梁归智等同志的不同见解,‘秦学’必得在坦率、尖锐的讨论中发展深化。”
但在大众媒体参与传播之后,学术争鸣忽然有了一种更简明易懂的理解思路:压迫/被压迫的二元关系。也因此,原本各种“非主流”的《红楼梦》研究,忽然有了更合适的位置来安置、阐释自己;而红学界板着面孔讲大道理的形象,绝对是公共危机应对的反面教材:顺势就被请上“权威机构”的高位,直到台下看热闹的人散了,才发现没有下来的台阶。
所谓“乱象”由此而生。纵观红学史,版本、作者、探佚……各个时期都有各种石破天惊的大故事出现,但红学界hold得住。刘心武给《解放日报》投稿时,编辑陈诏虽不认同,但亦认真编发;霍国玲《红楼解梦》出版时,胡文彬作序称“红楼不废百家言”。但这样的学术自信,在这个时代里渐渐被孤立,不再拥有话语权,动辄被“猛批”、“炮轰”所裹挟的红学会,不复存焉。
“面对别人的指责,我们现在是说话呢还是不说话呢?不说,他们就说:看吧,红学会无法反驳默认了;一说,他们就说:看吧,红学会压制围剿我们了。”红学会会长张庆善反问。
考证之窘,学术之困
从内部观察,失去自信或是因为红学界学术生产力的下降。红学家蔡义江介绍,他偶然读到一名研究者论《红楼梦》十二官的文章,此人考证出“官”用于人名自乾隆时期始,但没有展开,反是去阐释十二官各自的名字、角色等细节。
“这是一个很好的发现,可以有力地反驳那些说《红楼梦》写于康熙雍正年间的观点。但文章那样写,像是有一把好武器,却不知怎么用,最后朝天开了一枪。”出于纳闷,蔡义江问了下作者的想法,对方答:“我人微言轻,不敢接触这些论争。”
“这个观念就不对。就算两个权威辩论,你也可以表态:你支持谁的观点,或者对谁大部分同意哪里不同意,谁有问题但是哪里有道理。这里并不存在你人微不微轻不轻,而是你心里有没有存着学术上的大问题。”蔡义江说。
他感喟现在的年轻人研究越做越小。为了不出错,老找一些前人没有提到的小问题来做文章,“写文章就是要有自己的发现,写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。这么好的发现,你就随随便便用在一篇没人注意的文章里,这不是浪费嘛!”
对于一门成熟学科,这并不算新鲜问题,但红学因以考证为根本,此种现象格外显眼。红学一词的出现可追溯至光绪年间,但用以指称“用现代学术方法来研究《红楼梦》”,却是要到1921年胡适的《红楼梦考证》。胡适认为蔡元培等对《红楼梦》本事的猜谜方式是歧途,正确的方式是根据可靠版本和材料,确定作者、家世、年代、版本,其自道曰:“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。我要教人疑而后信,考而后信,有充分证据而后信。”
但考证方法,倚重的除了材料,还有学问功夫。毕竟不是手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就能负责阐释一切的上世纪50年代,年轻学者望之生怯或曰敬畏之心,也情有可原。更重要的是,版本与作者的材料已多年没有更新,翻来覆去的考证颇有些无米之炊感。而现今的索隐派“卷土重来”,也是因为考证派如今自顾不暇的窘境。
“现在的很多文章都在炒冷饭,把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东西拿过来,加点新名词,加点所谓方法的作料,就出来了。这还算好的。有一次我去《红楼梦学刊》办公室,看到桌子上有我一篇文章,再一看作者是别人,已经胆大包天到把别人的文章抄一遍,连小标题都不改就送来发表了。”胡文彬说。
1979年《红楼梦学刊》第一辑出版时,发行8.5万册,而现在跌至三四千册,这或可看做学界与大众已互不相干,但刊物的文章质量亦不复从前。一位学者认为,《红楼梦学刊》目前1/3的文章是没有达到发表标准的。
但主编张庆善认为,不可脱离当下学术环境来看红学及学刊存在的问题。“《红楼梦学刊》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是教育部认定的重要学术刊物,但它不属于核心期刊,因为定所谓核心期刊的标准是转载率,而《红楼梦学刊》作为专刊,转载率无法跟综合类刊物相比。这不科学,但现在衡量学术的杠杆就是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数量,很多学者要评职称,要面临生活压力,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情。”
学术研究与文化产品
《红楼梦学刊》第一辑发行8.5万册,第二辑11万册,但第三辑后,销量逐渐下滑。在当时,这未必是由学术质量引发,更大的可能是,读者发现《红楼梦》研究,并不是他们想象或习惯的那样了。
自流传时起,读《红楼梦》可能就有两套系统:“引车卖浆者流”的普通人往往满足于故事层面,而文人学士则更乐于在虚实掩映草蛇灰线的叙事中,衍生种种智力游戏;在衣食起居器物仪制的细节中,发现种种文化意蕴。在清代李放的《八旗画录》中,便记载“光绪初,京朝上大夫尤喜读之,自相矜为红学云”,颇见知识分子的自矜自许。
也因此,《红楼梦》在民间的传播,除了小说本身,依靠的是戏曲、评书、影视作品等强调故事性的文化产品,与研究作者、版本、家世、探佚的红学实为殊途。而索隐与考据再颉颃,也不过是知识精英间的分野,虽然如果向大众阐释,自然是蔡元培的隐藏很深的反清复明故事,吸引力会高于胡适的甲戌本庚辰本程高本之类令人困惑的名目比较。
但在上世纪50-70年代的中国,《红楼梦》不仅只是一部优秀古典小说,更因毛泽东多次推荐,是“文革”期间除了鲁迅与部分革命文学外,尚能合法阅读的文学作品,其意义与影响不言而喻。“全民评红”时,普罗大众运用阶级论的分析工具,一年之间在全国报刊上发了319篇评红文章。
因这段历史,《红楼梦》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,当下各种地方红学会里收纳的离退休干部,或许都曾共享这段集体记忆。而在上世纪80年代,红学研究并不曾脱离大众需求,比如使小说回归小说的作品解析、人物论,或当时流行的美学理论阐释。
1987年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(以下简称“87版”)也被看做是学界与大众文化需求结合的优质案例。胡文彬此前与该剧导演王扶林的夫人合作过广播剧《红楼梦》,因此当了电视剧的副监制——那个副字,是他自己要求的。五年之间他奔走于剧组与学界,每个月拿30元的车马费。
坊间流传红学界有周(汝昌)派与冯(其庸)派之争,在新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播出时,甚至演绎成诸如87版周汝昌任顾问,反对后四十回;而新版冯其庸任顾问,支持用程高本,因而导致两剧的差别等说法。胡文彬对此解释:“87版是整个红学会都支持的,三个编剧都是红学会推荐的。至于李希凡、冯其庸没当顾问,李是认为没有一个经典作品能够以其他的艺术形式改编成功,他不看好所以拒绝。而冯其庸是当时央视给他顾问名单请他签名,他说你等等,我看看。至于周汝昌,他那个时候其实在美国。”
冯其庸虽未当顾问,但87版受到学界批评的时候,他还撰文力挺,认为拍电视剧是对的。电视剧播出后,相关图书被抢购一空,冯其庸称之为“《红楼梦》小说有史以来最大的普及”。
或许因为这样的往事,所以“乱象”之时,红学家们仿佛才突然发现,很多普通读者、观众已不站在自己这边,学界与大众之间的文化联系及信任似乎不再。而在这个时代要重新接续,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产品之间,恐怕差了100个娱乐头条。当胡文彬看到有新闻称新版《红楼梦》需要让红学家审核剧本,不通过就不盖章,不盖章就没法拍,大笑之余,却又无奈:“我想红学会什么时候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啊,就算广电总局审,电视家协会审,也轮不到红学会吧,但媒体也就这么报道了。”
“当大众需要一种普及性的形式的时候,红学家没有及时站出来,适应大众的要求,因此这个舞台被人家占领了,当然就出了问题。误会越来越深,矛盾逐渐激化。在这一点上红学家要反思,要总结经验教训,思考怎么把小众研究转化成大众的文化产品。”胡文彬说,“希望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,红学能够恢复元气、走向正轨。而这首先要红学界正视自己的问题,去检讨去总结。我相信还是会好起来的。” 查看更多会考成绩查询相关内容,请点击会考成绩查询
推荐访问:
推荐文章